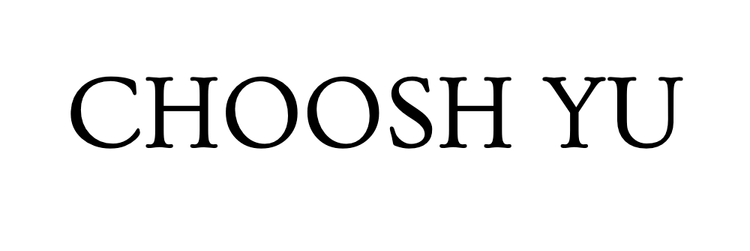凌晨四点半,深蓝色的天还在等太阳。这些天被太阳烤黑的皮肤在摩托车不断前行中沾满了海水蒸发出的雾气,又湿又凉。眼前的一切皆是虚焦,但也清楚。这感觉更像现在对于那段时光的回忆:虚焦,且清楚。COVID全球爆发前,在巴厘岛的Uluwatu住了2个月后,我回到加州的家和所有人一起Quarantine。打那以后,我好像不断在寻找那种虚焦且清楚的真实感。无牵挂,无事扰。我谁都不认识;谁,也都不认识我。在巴厘岛的日子我的生活除了寻觅海浪,便是每天固定的写作。好友曾说:独自沉浸于陌生的文化从某种角度来讲是一种类似致幻一样的体验。极度的陌生感和孤独感在无限美妙的视觉冲击下发酵,与时间齐舞,体会高低起伏。
海是静的,水是凉的,偶尔腿间划过暖流包裹裸露的大腿,那感觉有点像穿着wetsuit撒尿。海上等浪的人眼睛如海水,清澈见底,无限生机。和个把月前在北京看到的雾霾形成鲜明对比。一次京至沈的火车旅行中,我看着被雾霾吞没的大地写了一段场景。后来,这段场景在巴厘岛借着虚焦的真实感变成了短片剧本Suffocate。
旁晚,众人围长桌而席。Putu用米饭,日本咖喱和沙拉招待在外野了一天的这帮人。Putu的先生Stone出生在日本,大学时期曾在UC Berkeley读本科。他毕业回到东京后因受不了本国的生活方式搬到了巴厘岛。我在巴厘岛认识他的时候,他是三个孩子的爸爸,最小的叫Chisaki。几个常住他家的日本浪人加上我这个外国人就构成了当时的“海浪猎杀帮”。我不懂日语,与帮派其他成员的沟通仅限于“Morning”,“Go surfing?”, “Let’s GO!”。
又是凌晨,“海浪猎杀帮”成员山田,Yoshi和我在Stone堆满了冲浪板的小面包车里挤在一起。透过上了霜的车窗,那些虚焦的摩托车尾灯好像萤火虫,三五成群伴着我们飞到了很远的海边。商量好船费,太阳从水里爬出来,我们乘着木船去找浪。飞机划过头顶的声音有时与海浪Crash的声音重合,一高一低,起伏不定。巨大的浪墙移动着海水,随着远处的线逐渐变成山,海上聊天的声音被凌乱的划水声取代。那二三十个挺的溜直的胸脯上的脑袋随着山移动的方向而转动。飞快划水的一双双手把海面打的啪啪直响,那场面有点儿像一群天鹅集体奋力拍打翅膀挣脱地球引力一样,有意思极了。浪山瞬间到了眼前,我抬头只见一个人在山的顶峰转了身,并向我的方向拍动着他那双巨大的翅膀,还没等我来得及离开他的航道,他已经站在冲浪板上以极快的下坡速度飞到了我的眼前。我来不及duckdive,为了保住宝贵的头骨,一个侧身我滚到水里。任凭海浪把我高高托起,并重重的摔在水面上。然后便是只孤独的袜子和强进的滚筒洗衣机之间的爱情故事。不知道过了多久,我的脑袋终于浮出水面。没等我喘口气,第二个排山倒海也到了头顶,然后第三个,第四个…
午后,Chisaki认真的看着我的冲浪板上一掌之长的缺口,把眼睛瞪的大大的对我说: “Mr. Chang, that’s crazy! But I’m glad you are ok!”,然后跑去草里捉虫子。 我看着被那人撞坏的豁口,想起刚才死里逃生的一幕和那个差点没给我脑瓜子干开瓢的二货说的话: “I don’t have a phone! Oh, come on dude, we are both from California, plus you can fix that for $30 dollars here in Bali. You are seriously gonna chase me down for $30 bucks? ” 。我心想:你是加州出生的, 我是个移民。虽然这本不应该是区分你我的标志。
又一个清晨,小面包车里Stone和我坐在前面,后面是一车印尼孩子,唱了一路我听不懂的儿歌。车子慢下来,Putu和Stone说夹着印尼话的日语。Stone停车后掏出手机,冲着远处渺小的火山拍照。只见浓浓的黑烟挂在巴厘岛的最高点。那应该是我第一次看到运动中的活火山。活动的火山伴着听不懂的儿歌,我盘算着写作的心逐渐消失了,也跟着哼起了那些不知其意的调子。瞬间士气高昂,孩子们扯着嗓子以近乎哀嚎的方式把气氛蔓延到了车外,消失在萤火虫排出的二氧化碳中。今天是Putu娘家的祭祖典礼,是个从清晨就开始了的重要祭祀活动。车上的孩子都是表亲,他们现在正在换祭祀的传统服装,我当然也被拉到其中。行头上身,我立刻人模狗样的端起杯子与一大家老老少少喝起了Tuak。一杯接一杯,米香和奶香伴着淡淡的涩,在正午的太阳下显得甘甜无比。高僧在院子里的高台上念经,大家由Putu的妈妈和姑姑轮流按照顺序在高台下做着各式各样的祭祀动作,直到夜里。
深夜,微凉。我在一个头顶银河繁星的供台上醒来,发现身边睡的全是陌生人。我在哪儿?我问自己。伴随着晕眩,我抬头发现“海浪猎杀帮”的Yoshi酣睡在不远的草地上。Tuak!对了,我们一起在Putu娘家喝的Tuak!闭上眼,那些对于巴厘岛的回忆好像一些表面看起来并无关联的片段,但究其深处却一脉相通。睁开眼看着这些照片,诸多细节以虚焦的状态投射在眼前,好像那些故意被剪掉藏起来的场景。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太阳,升起来了。
写于 Oak Park, California
Oct, 2021